老鼠
作者:liufiel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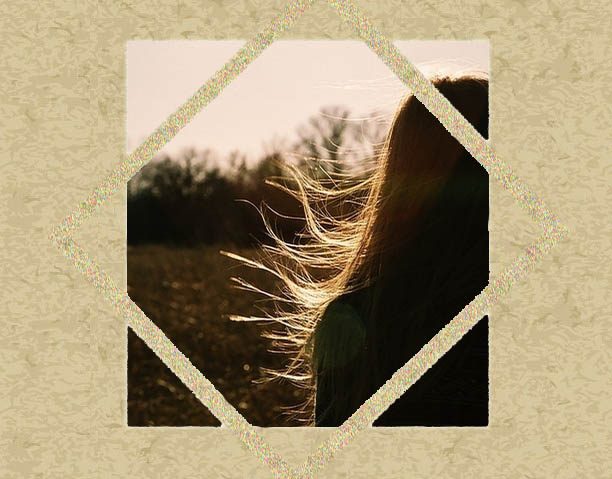
在没有认识老鼠之前,它先进入了我的胃。
七十年代初,一个饥饿的年代。我差不多吃光了父亲的藏书,那些书换成白花花的米,磨成粑粑,填充我饥肠辘辘的肚肠。
有一天,母亲从热腾腾的小铁饭鼎里手忙脚乱地端出我专用的小瓷碗,她把小瓷碗飞快地放在小桌上,迅速拿手指摸自己的耳垂止烫。我好奇地凑近一看,小瓷碗里居然有一小堆肉,母亲说:“嫚子,有把把(第四声)吃喽。”我们这方言哄小孩把吃肉说成吃把把,比喻鸭把子,鹅把把什么的。香喷喷的肉送进了我贪婪的嘴巴,我捧着母亲给我的小瓷碗,吃光了碗里的美味。母亲说:“这是老鼠把把呢,下次再让你爸抓个老鼠,剥了皮蒸给你吃。”
当时的我很幼小,小得讲不全一句话来,也不知老鼠何物,只觉得那老鼠把把无比的香,无比的好吃。吃完后,还不时地期待着再一次吃到老鼠把把,当然,那时也吃过青蛙把把,鱼把把什么的,总之现在想起来,那些全是一个味——好吃的把把。
后来长大些了,看到屋里偶尔出现老鼠,时而像幽灵那么一窜跳,时而在深夜啃什么家什,有点恐惧,母亲便笑:“你还吃过老鼠肉呢!”母亲这话差点让我把多年前的那堆老鼠把把给呕出来。从我认识老鼠起,便对老鼠有一种强烈的厌恶感,不仅因为老鼠总是暗地里偷偷摸摸地咬东西或是突地窜溜。更让我产生厌恶感的是我的胃里曾经有它的肉,我那时居然把它的肉当成美味吃得津津有味,想起都觉得恶心,对过去吃老鼠把把的情景有些不堪回首。好在小时候吃老鼠肉时,并没留下什么更深的印象,才终究让恶心只成为一种感觉。
小时候家里没有书柜,父亲幸存的一些藏书都小心地堆放在床顶上,那时候的床是老式木床,顶上有薄木板儿。自从我发现了那些书之后,就经常沿着床端的梯坎爬上去,悄悄地选几本书下来看,看完了,又不动声色地放回去。于是,我经常发现书上有一些粒状的老鼠屎,呕心极了,但因为爱看那些书,只得忍耐那恶心的鼠味。
俗话说“老鼠过街,人人喊打”,人们对老鼠的厌恶是由来已久的,我也不例外。对于老鼠的味道,我的鼻子显得格外敏感,比喻屋子里突然出现的鼠味、被老鼠咬破的物什,或是碎纸屑、老鼠屎尿什么的,只要一看到这些或是闻到味道,我就会产生狂躁气闷,惶惶不可终日。这些年住在丈夫单位,庭院宽大,杂屋渠沟垃圾箱绿化带,都是老鼠的新房。因国家禁止用“毒鼠强”一类的剧毒药,更使老鼠泛滥成灾,一窝窝群出群没,大的起码两三斤,小的脚拇指那么大。无论大小,这些老鼠们一概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窜撞。由于单位房间少,杂物多,尤其是我的书因为书柜有限、空间有限,堆得到处都是。给这些大小老鼠创建了藏身之处,它们时常在深夜里吱吱欢歌,快乐地啃咬我那些宝贝书籍,把我恨得牙根痒痒。
一天,丈夫下乡归来,手上拿着几张“神猫”粘鼠板,我们费了好大的力气,将粘折在一起的纸板拉开,粘鼠板里面是具有超强粘贴力的物质。我想这东西应该是根据蜘蛛丝的特征发明的吧,手拉纸板时不小心碰到粘液,擦不去洗不掉。第一天只捕获了几只蚊蝇,落入粘鼠板的蚊蝇翅膀扑闪几分钟,便命归黄泉。第二天,我将粘鼠板放置一只小老鼠经常窜梭的路经上。果然,下午,这只涉世不深的小老鼠就落入陷阱,被粘住后,小老鼠愤怒地吱吱大叫,我估计它在咒骂这个粘鼠板上的粘液。它开始条件反射地挣扎,一挣扎,粘液便将它身上的毛粘脱,痛得它吱吱乱叫。接着,它用四条腿费力撑起,想站起来,可是着点被粘液死死粘住,一动就牵动那一块的体毛和皮肉,就连本来没被粘的腿,由于想支撑,也被牢牢粘住了,我能想象它的那种疼痛,可我不能救它。小老鼠使劲地挣扎,可是,越是挣扎却被粘得越紧。许久,小老鼠耗尽了能量,感觉到害怕和急躁,开始嗯嗯地大声哭喊起来。四周的老鼠都没有出现,谁也没有来看它救它。小老鼠就这样孤立无援地哭了好一阵,渐渐地,它越来越虚弱,只小声地呻吟,无望地趴在那儿,时而发出一小阵绝望的声音。第二天早上,我去观察那只被粘的小老鼠,发现它已垂下无力的眼皮,眼睛里没有半点生气,我不知道它是活着的还是已经没有生命了。而被同时放置厨房边楼梯下杂物旁的那张粘鼠板上,已经粘上了五六只那样的小老鼠,一定是同窝的老鼠兄弟姐妹,或许,它们有的是不小心跌入,有的是好奇去拉,有的是舍死相救,总之,它们都没逃脱被粘住的命运。
这样一场运动过后,房间恢复了安宁,我又恢复了正常生活,放心大胆地主宰小屋。有时不免产生一些想法:假若老鼠也像其它被宠动物一样,被圈养、被照顾、被爱,那它们是不是会改变偷盗或是磨齿的习性?假如它们移居山野,不贪恋人气,是否又是另一种命运?或者,老鼠们像蚂蚁那么卑微地活着,是否可以远离人类的捕杀呢?


